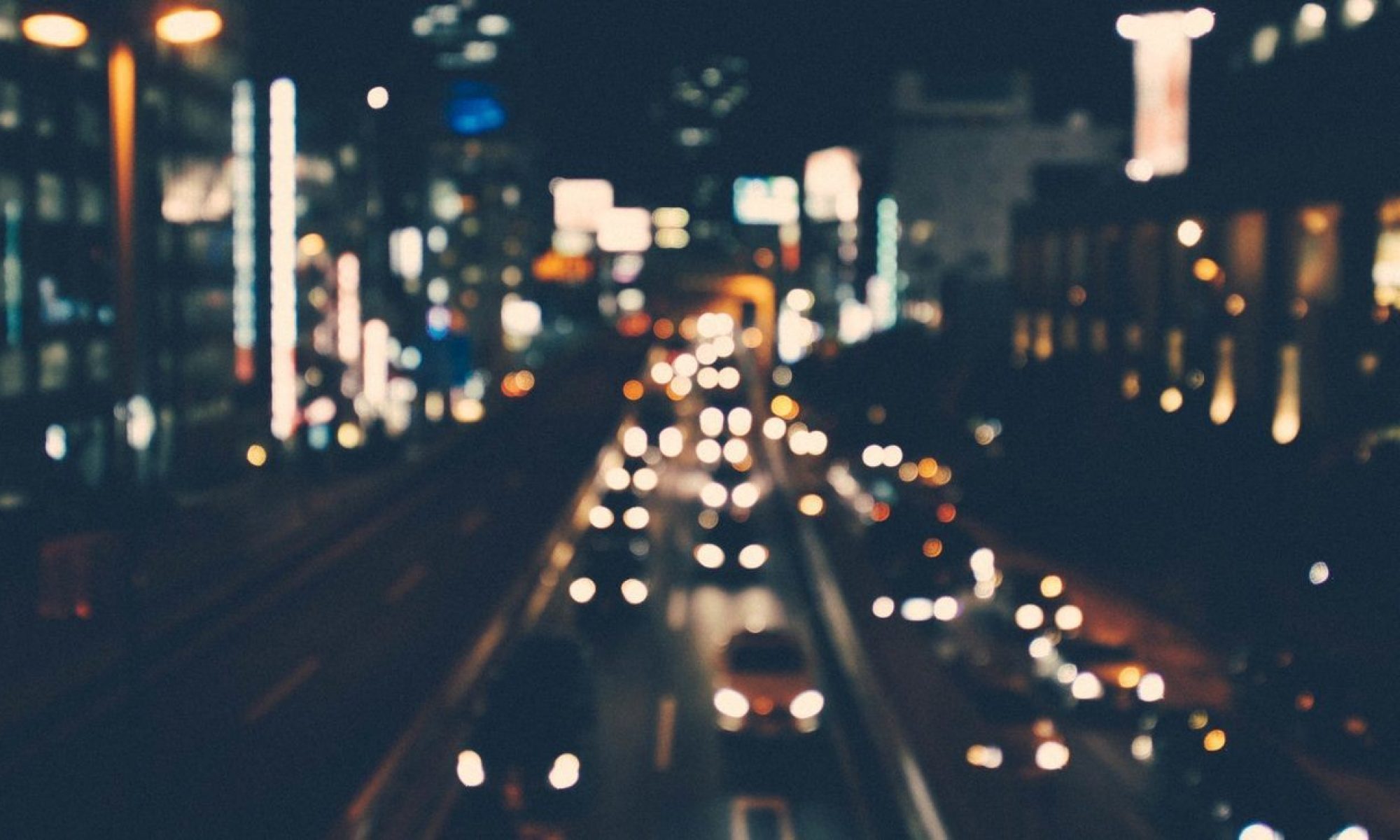冬天的时候,那个时间应该是数九里面的五九末,六九初这个时候,也记不清个大概。那天想吃关东煮,类似于烧烤一样的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不记住是烧烤这种东西的话,我怕我忘了烧烤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本来我对这种东西是比较排斥的,那天确实无聊,想自己出去买点吃,完了我娘非要陪我去,原因就是怕我出去之后不再回来,男的出去可能比较放荡,主要在时间方面没有概念。所以以陪我买关东煮的名义来监督我,我感觉有点好笑而且有点可爱。好笑就是如果我想出去,应该没人能拦得住。可爱就是,她竟然有这种想法,从她有这种想法之后,就算我有出去不会来的想法,我也不会出去了,我自己也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到了烧烤摊儿之后,我大步奔到第一家那个摊位。因为经常不在家或者家乡呆着,不知道哪个好那个坏,或许是不知道好坏。
完了我告诉我娘就这家吧,我娘说去里边吧,那家比较好吃。
随便吧,哪个都能成,就这一家子吧。
那能成,就在这儿买吧。
到了摊位,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本来自己对吃的这种东西不是特别在意,就是兴致来了,想出来买点再回去的,说不明白是什么想法,本来所有的东西都很矛盾。完了我娘说吃这个,这个有助于消化。吃这个,这个晚上了,吃完不是那么重。重,就是东西不会在肚子里或者胃里积压,毕竟大晚上的。我随着我娘的建议挑了几串,完了我自己又挑了几串。挑完之后,我问老板娘多少钱,因为整个摊位只有一个女的,没有男的,如果有男的,我可能会问老板多少钱。因为在关中地区,男的就是掌柜的,不管有没有生意,就是在家,他也是掌柜的。
问完价钱之后,老板娘告诉多少钱,我娘从插口里掏出她说的那个数目,给了老板娘。钱不重要,重要的插口,插口就是外边人说的口袋儿。老板娘拿着我们挑选的关东煮的串儿开始放在一个长方体的铁的容器里边煮,铁的容器下边是煤气灶,没有人的时候他们煤气灶开的特别小,生怕有人来了之后容器里边的汤凉了;开太大怕太费煤气,这也是成本的一部分,本来就是小本生意。
老板娘一边将我选的东西放在铁容器里边煮,我只能用铁容器去形容了,其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毕竟整个摊位只有我一个顾客,也就是我们的买主。煮的时候她还将竹签没有串起来的东西由零串整,这个整就是一串。完了我娘问,你一边串一边煮是把。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出来是这样的, 但是关东或者整个西北地区的解除尴尬,或许是为了有点说的东西让彼此不要那么陌生,问这些一眼都能看出来的问题。这不是做作,他是西北的一种朴实,这种朴实就像黄土一样,孕育了好多的麦田,玉米,甚至于有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儿。
老板娘说,是啊,反正煮的时候也没啥忙的,就一边煮一边串了。这是她和我娘的对话。
那这些已经串好的你是撒时候串的呢。
这是我白天串的,白天起来的比较早,家里边有娃娃,还有老的(老的就是自己的父母,甚至于爷爷奶奶,毕竟终于传统社会的人们结婚比较早,所以四世同堂是很普遍的,)。早晨起来,做好干粮。(西北地区将早餐叫做干粮。)伺候着老的吃完,喂完娃娃吃完,老的就躺着或者在院子里晒太阳。娃娃哄他们睡着,自己就开始打扫屋子。等到打扫的差不多,也就下午一点多或者两点钟了。(只能在这个区域之间,她们做什么东西都是有规律的,因为习惯了,就算自己不乐意这么做,超过或者早于这个事件老的也不会习惯),一两点钟完事儿了,家里又洗的东西就洗洗,没有的话就开始串关东煮的串儿。等到串完东西之后已经是下午的五点钟,或许能多一刻。完了我又做下午吃的,面条,臊子,都是自己弄,等到熟了之后,等老的吃饱,完了告诉娃他奶,(也就是她口中的婆婆。)给娃喂饭吃,我出去摆摊了。于是我就出来了,六点钟必须在这个地方摆开了,如果没来的话就会被别人占了,则的人你也晓得,都比较霸王,所以宁愿早也不能迟。
也对,则的人本来是这样,因为只会注重自己的想法,从来不在乎社会的感情。‘则’也就是现在,所以这是我们那边从秦文化发展过来的一种方言。这种方言除了朴实之外我根本想不出别的词语来形容。
她说完洗洗东西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句,屋里掌柜的出去打工了,也剩下自己了,自己不做,屋里老的小的吃什么啊。其实也对,有些事儿自己不做,也没有人做,有些东西自己不去主动,没人等你。
我娘说,看来你家里人口很多,那一般晚上几点收摊。我娘问这句话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这些个东西,我也没想过那女的是自己一个人六点之前出来摆摊,于是我惊讶了。
那女的说,生意好的时候,冬天可能十一点半就收摊,夏天可能两点前后就收摊。等到她说完这些话之后我更惊讶了,我惊讶的不是她有多么敬业或者对生活有多么憧憬,我惊讶的是别人都能这么做,甚至于一个女的都能这么坚持,为什么有时候我会感觉到累,或者那种莫名的失落,所以我感觉这家的关东煮应该是最好吃的,味道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酝酿的那种苦才是最朴实和醇香的。
说了差不多7分钟左右,为什么说七分钟左右呢, 因为我对时间,节气这个东西记的特别清楚,如果我记不住这些时间的话,我可能会记不住这些时间里边所发生的那些事儿。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记住这些东西,可能是和每个人的境遇有关系吧,再别人看来就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但是我感觉我记忆犹新,每次我都会想想,就像每次我会想起看一看夕阳一样,但是每次想起的时候都不是晴天。
我娘说,那还能成,则屋里都放不下,但是生活的小事(柴米油盐)还得自己挖(争取或者把握)。
完了我和我娘就回家了,回家我吃这家的东西并不是特别好吃,其实本身我是尝不出来有多好吃,因为我没吃过别家的,毕竟没有对比也没有好坏。吃完之后味道我根本没有记住,记住的只是她和我娘的对话,毕竟是别人,可能我娘也是这样,所以我想怀念一下我娘小时候对我无私的照料而不是照顾,照料可能是生活和做人方面的东西,照顾只是生活之中的一些而已。
我从三岁在城里读书,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感情比较丰富的人。其实每个人的感情丰富才能提现出对身旁所有一切的洒脱或者狠心。毕竟离开我娘时间比较多,与其说离开的时间比较多,不如说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因为很少有人说离开,这个东西太敏感,别人接受不了,我从小就接受了。所以有什么想我娘的时候,我会寻思,我寻思,这辈子是我最有福气的一辈子了。
那时候对节气一概不知,只知道该是开花的季节,一定是春天到了。老家种了好多的杏树,不同品种的,有大有小。也不知道是自己家里种的还是自然生长的。惊蛰以后,家里后院的杏花都开了,粉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香味扑到前院,前院有两棵大的梨树,梨树的花是白色的,好几种香味掺杂在了一起,给乡下的宁静中填满了生机。仔细回想,自己已经有接近十多年的时间没在家乡度过春天了。
等到了清明和谷雨之间,花已经败了,但是绿叶又出来了,乡下从来不会给你一种失落的感觉。我平生最怕失落了。等到绿叶生长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该吃野菜的时候了,苜蓿,荠菜(荠荠菜),蕨菜,香椿等等。本来是百花齐放,绿叶倍长的时节,但是家里还是比较忙的。
当时家里种着菜子,也就是现在山西婺源所说的油菜花。毕竟有些东西太浮夸了显示不出她的朴实。还有小麦,玉米。等到清明前,先给菜子地里除草,那会我在小县城里边,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或者知道也没有在乎或者根本无视,因为每个时段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清明前我娘给菜子出完草之后,等到清明后,几场雨下完后,再给小麦的地里除草。小麦地里除草不是一遍,至少得两边,我娘会除三遍,因为当时家里比较清贫,生怕秋来到收成比较少,过不了冻,怕家人挨饿,其实那会儿已经没有挨饿这一说,可能是生的时代不一样,生于忧患的意识不能磨灭。等到我娘除完小麦地里的草之后,又开始为玉米地除草,东北管玉米叫包谷,他们总感觉这种东西是廉价的。但是殊不知在西北地区有很长一段时间玉米比人们经常吃的小麦更能卖出价钱。玉米地里边的草是特别长的,而且根本是特别牢固。除草不一定给茎部割掉就行了,必须得连根拔掉,不然她的生命力特别顽强,等到拔掉茎部之后,不到一周时间又长出来了,而且比玉米更加繁茂,是不是有些事儿必须得刻意,所以让人难以捉摸。我娘会在行玉米地膜之间看见不同的野草,然后连根拔掉,等到拔掉一下午的时间之后,我娘的手也变绿了,绿的时间久了也就有了茧子了,有了茧子之后也就有了沧桑了,有了沧桑之后也就有了生活的沉淀了,不为别的,就为生活,毕竟她在玉米地除草的时候不用锄头,而且不会浮躁。
等除完草之后,晚饭吃完,她回去场里扯一籓笼麦草,为了烧炕引火。也就是填炕了。乡下睡的都是火炕,虽然有点硬,但是睡久了感觉踏实。炕是每个季节都要去填的,土炕如果不去填,不去点着烧的话会特别渗骨头。搁置麦草的地方和住的地方还有一段路程,农村那会儿已经能看见了漫天的星星。我娘自己拿着籓笼出去场里扯一些麦草,然后提回来。
那会儿的天已经昏下来了,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漫天都是星星,清风扑面,还能看见湛蓝的天昏渐渐变黑,这一刻是从未有过的惬意和安定。麦草只是引火的,因为它容易着。将麦草填进去之前就得塞一些茅草,我们那边叫茅衣,大概就是不用正儿八经去积攒的一些茅草。春夏塞的时候茅草,等到秋冬会有牛粪,因为牛粪燃烧的时间久,所以后半夜不会那么冷。塞完之后再将扯的麦草塞进去,点燃麦草之后,茅草顺着会慢慢的着了。一天该做的我娘基本做完了,可能晚上会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还得她去弄,但是她从没有过对家庭的或者社会不公的抱怨,从来都那么平静的做完一件事。其实理想这种东西每个人都是有的,我娘只是想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劳动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种理想叫做无私,单纯的想让我们这个家好起来,想让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可能她自己也没想过后来会是什么样,至少今天的东西做完她是踏实的,一天天这么踏实下来她的理想也就实现了,价值也就提现了。从每一件微小的事中表现出她无私的旷爱,可能就像路遥说的,每个平凡的人都有一个平凡的世界吧,这个世界可能别人不会懂,但是自己每天坚持劳动就行。
等到麦子地,玉米地里边的草除完之后,谷雨也已经过去了,夏至到来了。我娘会去县城里边赶集,赶着逢集的时候。集都是2,4,6这么分的,至少我们那边是这么样子,其他地方可能回事按照月份计算的。
赶集都干些什么呢,就是为了买一些鞋底,买一些布,针线等等。鞋底都是一些报废的大卡车轮胎割下来的塑胶做成鞋样儿的平面,布主要是纳鞋肚,有清布,还有黑色的,比较久远的人家可能会用一些丝绸的东西去作为鞋肚为了显示身份。针线更不用说了,连接这些鞋底和鞋肚的中间这,如果没有这个线,可能没有布鞋,如果没有赶集,我不知道城里的生活这么好为什么要在乡下这么琐碎。
买完东西之后没有急着做布鞋,因为有跟重要的东西等着我娘去做。我家里边有一片果园,等到清明后必须得打农药,怕一些虫子将果园的树破坏了,等到秋天没有收成。毕竟啄木鸟是有限的,而且啄木鸟不一定是为了捉虫子。其实家里种果园不是为了有水果吃,而是上一辈的时候就有这个果园,不能在自己手里将果园农田化了,缺粮食是实际的,水果吃不吃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周末我放假了,回到家里,乡下的家里,我总感觉我不适应这个地方,因为我排斥,我怕我是乡下的,我会表现在我不会做这些东西,我会表现在我不去做这些东西,我会表现在我不去做这些东西,我会排斥,而且这个排斥叫做强烈。我娘会兑好农药。当时的我娘比较年轻,背也挺直。
兑好农药之后我跟着我娘去果园里边给果树喷农药,记得当时不是放暑假的时候,应该是某几个周末。背着一个绿色的农药箱,完了右手拿着喷头,左手打压,因为没有压力农药或者水质的东西是喷不出来的。每次喷农药的时候我感觉我是最轻松的时候,因为没自己什么事儿,我娘在那边喷药。我会站在捱边里,也就是崖边儿吹着小风,看着下边的麦田,玉米,对面的大山。一切总是那么和谐且惬意,风好暖和啊,毕竟自己是过来玩儿的。等到喷药箱我看见没有多少药水的时候,我会告诉我娘来我添点儿,但是我娘会说,你赶紧到一半个去,也就是一边儿去,农药有毒,我已经沾了,添药的事情我来。完了我看着我娘添完药之后,又将一整箱的农药喷完,我特别开心。我的开心不是因为给所有的果树喷药的,我的开心是我又有一箱农药的时间去吹吹风,坐在捱边里看看捱下边的东西,毕竟一切都是新奇的。因为在小县城读书没有接触过,或者有机会接触的时候比较抵触。当时是多么的幼稚啊,那种幼稚遇到我现在的脾气可能能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等抽完大嘴巴子手离开脸部的时候有几股红色的印记。
喷完农药之后,回家我娘就洗完手。家里边还养鸡了,给鸡拌食,拌完之后给我们做饭吃,从来不知道累怎么写,因为我娘没读过书,从来不知道累是什么,因为她是一味的付出。读书了又能怎么样,对世间没有憧憬,没有朴实的勤劳和魔鬼有什么两样,毕竟魔鬼还能出来吓吓人。回报又能怎么样,一个朴实的勤劳者不计任何回报都能这么做,现阶段的为人民服务回报岂不是多了去了,做了什么,除了我看到的贪欲之外。
就这么夏天一天天的过了,等到白露前后,家里开始琢磨收割菜子了,也就是菜花。北京人只知道菜子能生长出菜花,也就是油菜花,他们会利用油菜花去拍一些婚纱照,当做风景去看,殊不知最美好的风景是朴实的耕种和收割时节的那种喜悦。菜子是一种比较矫情的东西,如果收割早了,那么她会是瘪的,榨不出多少油来,农民这一年等于白忙活了。如果收割的完了,菜子会从壳里边炸出来,等到收割的时候就剩下了空壳,所以得把握好时机,这种时机只能在朴实且有经验的农民身上体现出来,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收割了,什么时候该撵了,都是对生活的一种阅历,有些东西不一定是人人都能完成的。
等到菜子收割之后,也就是小暑的时候,完了就开始撵菜子。本来每家的菜子也没种多少,最多也就两亩地。我家应该种了一亩半,在我的印象中,也就是现在所谓的1000平米左右。撵完菜子之后不能装在麻袋里边一直放在,这样会发潮。麻袋也就是大一点而且结实一点的袋子。得等到一个晴天拿出来晒菜子,这样晒过的菜子既不会潮而且能炸出油。撵菜子的时候大户人家会开拖拉机拉着一个橹齣去撵,属于半人工。但是家里边没有拖拉机的,而且种的比较少的,会拿廉菅去拍打。橹齣类似于一个柱体的石头,明朝就有这种东西,遗传至今。廉菅类似于一个长方体的模板,但是是中心是有零希的空格,长特别长,宽有三十厘米左右,来回拍打,等到感觉菜子壳里边的菜子都出来之后就不用再卖力拍了。一亩地也就能种2麻袋菜子,等到晒完之后也就是150公斤左右,150公斤的菜子能炸60-70左右的菜子油,也够一个冬天加下一年的春天来食用了。
我记得每次这个时候我娘拍打完菜子之后晚上睡觉就说胳膊疼,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会疼,这种不理解建立在我胳膊不疼的基础上。而且每次拍打完之后我娘会去给我们做饭,做完之后我们围着一个小石桌一家人吃饭,头顶是一颗上了年龄的梨花树,叶子绿的能出油,想摘一片的时候但是又不忍心。晚上睡觉大家都在一个炕上睡觉,土炕。等到我感觉迷糊的时候,隐约能感觉到我娘翻来覆去睡不着的那种难受,但是难受中夹杂着一点希望,毕竟我在她旁边睡着,从胎儿一直到一米多。这种期许和牵挂根本没有任何粗俗的东西夹杂在里边,或许这种夹杂是金钱,或许名,或许照顾尽孝关心之类的,总之是回报之类的东西,根本没有。
小暑过后,半个月之后就是大暑,大暑过不了几天就开始割麦子了。这个时候就是最忙碌的时候,这个忙碌不是浮躁,也不是着急,是因为糊口和期望。家里出了种玉米多之外,小麦比玉米更多,所以每年到了收割小麦的时候特别隆重,这种隆重不是多么华丽,而是人多。例如谁家的麦子多了,可能会喊一些街坊过来帮忙收割,等收割完了之后再去脱麦子。所谓脱麦子也就是将麦草和颗粒分离出来。但是这种喊不是无偿的,而是等到自家的麦子收完之后,别人帮咱了,咱再去帮别人收。因为麦子不会像菜子一样那么矫情,麦子根据每块地种的不一样成熟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会辫(pian)工。pian工就是别人帮自己了,完了自己帮别人。这也是收麦时间忙碌的一种表现。就算自己家的麦子比较少,不需要pian工,但是关系特别熟的街坊也得过去帮忙,这种帮忙不仅是表现在收麦子方面,而在做饭方面。
男人们一般都在场里脱麦子,女人们在家里为男人们做饭,这顿饭不像往常的饭一样,不仅要做的体面,而且要做的实惠,让大家吃饱。脱麦子的时候至少有十个人左右,加自家人应该有十五六,这么多人的饭,既要可口,而且要大气。这就是农民人的朴实,也是农民人的对生活的一种责任,那种积极向上可能在黑暗中都能看见阳光,就算没有阳光也能大步向前。
每次我娘帮别人家做晚饭之后,回来还得为我们家做饭,或者会低头找别家脱麦主人要一些今天的饭,回来让我们吃,如果吃不饱可能还得做。我娘的这种做法我记忆犹新,但是回来做没做我有点模糊,我怕记住了我娘会累,我不想她太累。这就是我娘,每次告诉对我最大的期许是吃好,身体好,这就是我娘,用朴实,幽微的话语和行动告诉我最博大的爱。我想我娘了,我想劳动节过来看看她,因为她每天都在劳动。
冬天……有点回忆不下去了,喝完酒之后总想掩饰点东西,其实喝完酒才是表达最清楚的时候,等到冬天的时候,我用最洁白的雪擦去我娘身体的负担,让她健康。
可能那个关东煮的境遇是我娘的一部分影子,这个影子从挺值的背最后变得佝偻,完了步伐也变得蹒跚。生活本来给她变成这个样子,她没有任何埋怨,只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不怕鞋子破烂,不怕道路颠簸。我娘用最朴实无华的行为洗涤着我们的心灵,我想我娘了,我想那个为我操劳而到白头的,每次回家为我做好吃的,有什么事儿自己扛了反过来安慰我的娘了。我娘表现出的那种刚强,然后表现出对我的支持,那种对生活的希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每时每刻没有回报的做出来的,她的梦想就是劳动之后天气会从阴天转晴,这就是我娘,我爱的娘。
最后我在外边上学了,我总感觉每一次要么不要重逢,要么不要分别。等到我在外边呆了几年之后,每次回来都想尝试着改变多点时间陪我娘,但是我错了,有些东西年岁不到那个数字是改变不了的,但是至少以后我会去朝着这个方向做,毕竟事情是会改变的,现在不做,以后也没机会去做,但是庆幸我现在有机会去做。遗憾的事情会让人感到失落,我这辈子最特么讨厌失落。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出门的时候都吃不下东西,但是每次出门之前娘会做好多东西,可能是她习惯了我每次都这么赶。因为她知道我吃不动,就算摆在桌子上看着,她也是开心的,毕竟我在她身边一起看着桌子上吃不完的饭菜。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走的时候都得找朋友一起聚一聚,喝点酒,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在当前这个境遇再坐到一起了。境遇这种东西每次回来都有,娘只有一个。
上次回家是冬天,离开也是冬天。冻得通透的冬日,大街上摆着零零碎碎的几个小吃摊儿,没有逢集时候那么喧闹。人行道上的槐树突兀着,嶙峋的树干上伸着几支干秃秃小树枝,看着多么的冷漠啊。今天是个晴天,她与她的枝干在明镜的蓝天下伫立着并且相互映衬着。时不时刮来一阵风,吹起街上的尘土。要不是今儿是个大晴天,真是透骨的冷。这就是她的家乡,温暖的朝阳和凛冽的北风。 等到车开出几公里以后,我能感觉到她眼睛流向眼角的泪水已经被离别的风吹干。
从春秋与冬夏,从朝阳到日暮,这是永不止尽的付出,这种永无止尽的付出她叫无所回报。我不怕忘了这些事迹,我怕忘了这种不要回报的付出。
过了分别也是下一次的重逢,毕竟不是分离,只是想我娘了,魔鬼并没有多么煽情。